- 首頁(yè)
- 民文

- English

- 舉報(bào)專(zhuān)區(qū)

- 登錄
成都隨處可見(jiàn)!能造紙的鈔票樹(shù)被誤解了千年……
東漢時(shí)期
蔡倫利用構(gòu)樹(shù)皮發(fā)明了
聞名世界的造紙術(shù)
古人曾經(jīng)把構(gòu)樹(shù)稱(chēng)為楮
構(gòu)樹(shù)造的紙也被稱(chēng)為楮紙
北宋時(shí)期發(fā)行的“交子”
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
就是用楮皮紙印制而成
直至今天
日本紙幣仍是用楮紙制作的
這個(gè)能造紙的鈔票樹(shù)
為什么又背負(fù)了“千年惡名”?
↓↓↓
01
構(gòu)樹(shù)與交子
川西壩子土地肥沃,上億年的造山運(yùn)動(dòng),使四川盆地這個(gè)碩大的盆底,似聚寶盆一般,成為名副其實(shí)的天府之國(guó)。這里的農(nóng)民隨手在地上抓一把油黑的泥土,拿到西北地區(qū)都是上好的肥料。
天地玄黃,宇宙洪荒。在時(shí)間以千年、萬(wàn)年為單位的宇宙浩渺和混沌時(shí)期,天與地在黑暗中逐漸變得明朗起來(lái)……處于青春期的地球,曾一度進(jìn)行著活躍的造山運(yùn)動(dòng)。當(dāng)青春期進(jìn)行到三億六千萬(wàn)年的時(shí)候,四川盆地特殊的地貌結(jié)構(gòu)便已然形成。“北依秦嶺主峰,南靠云貴高原,西臨青藏高原,東向長(zhǎng)江三峽……”這是一個(gè)巨大的盆地,只有一個(gè)出口,那便是夔門(mén)。而成都,正處于這個(gè)盆地的盆底,四面都是淺丘、深丘甚至高山,而中間則是地勢(shì)開(kāi)闊天造地設(shè)一般的千里沃野成都平原。
冬無(wú)嚴(yán)寒,夏無(wú)酷暑,四面高山環(huán)繞,平原風(fēng)調(diào)雨順。成都以其雨水豐沛,氣候溫潤(rùn)而促催萬(wàn)物瘋長(zhǎng)。不僅是大熊貓?jiān)谶@里舒適地頤養(yǎng)天年,許多植物也在這里安了家,成為永久的居民。無(wú)論是城市還是農(nóng)村,有一種樹(shù)笑爛了臉,在這溫潤(rùn)的土壤里肆無(wú)忌憚地瘋長(zhǎng),隨處可見(jiàn)其子孫后代的影子。
它的名字叫構(gòu)樹(shù)。這不,成都東門(mén)專(zhuān)門(mén)有一條街,就喚名“構(gòu)樹(shù)街”。作為交子(北宋時(shí)期的一種紙幣)唯一量身定制的原材料,構(gòu)樹(shù)看似平凡,卻有著不凡的貢獻(xiàn)。
為了對(duì)它表達(dá)足夠的尊重與敬意,北宋初年時(shí)期的交子,就特地命名為“楮幣”(構(gòu)樹(shù)又稱(chēng)楮樹(shù))。千年過(guò)去了,直到現(xiàn)在,由構(gòu)樹(shù)皮制成的紙,還稱(chēng)為楮紙。
構(gòu)樹(shù)是成都平原極其平常的一種樹(shù),因?yàn)槠渖?qiáng),成都人往往又用一個(gè)通俗的“賤”字來(lái)形容。這里的“賤”不帶有任何貶意,自然是親切的稱(chēng)呼,主要指繁殖力強(qiáng),不計(jì)環(huán)境不計(jì)時(shí)間與空間,在成都平原這個(gè)水旱從人的溫潤(rùn)土壤里,都好養(yǎng)活。或許因?yàn)榉敝沉μ欤吹靡?jiàn)的瘋長(zhǎng)。從而影響了其他植物,固而人們每次看到一片構(gòu)樹(shù)長(zhǎng)出,就會(huì)拿刀砍伐,還不時(shí)會(huì)搭上一句,“這樹(shù)子,太賤了。”
查閱了一下相關(guān)辭典與史料,獲得有關(guān)構(gòu)樹(shù)相關(guān)的專(zhuān)業(yè)常識(shí):
構(gòu)樹(shù),古時(shí)稱(chēng)榖、楮樹(shù)、谷樹(shù)等。產(chǎn)于中國(guó)南北各地,南亞北部、東南亞、東亞等國(guó)家也有分布。
構(gòu)樹(shù)一般喜歡濃烈的陽(yáng)光,根系具備生長(zhǎng)快、萌芽快、分蘗強(qiáng)等特性,構(gòu)能同時(shí)適應(yīng)中國(guó)北方寒燥和南方暖潮的氣候。
構(gòu)不挑土壤,耐干旱瘠薄,也能生長(zhǎng)于水邊,多生長(zhǎng)于石灰?guī)r山地,也能在酸性土及中性土壤中生長(zhǎng),還可于鹽堿地,乃至污染嚴(yán)重的工地正常發(fā)育。
構(gòu)的韌皮纖維可造紙,果實(shí)可生食,也可釀酒,《本草綱目》載,果與根共入藥,補(bǔ)腎、利尿、強(qiáng)筋骨。嫩葉可作為飼料喂豬。
構(gòu)樹(shù)砍伐后,恢復(fù)速度快,次年又可以重新生長(zhǎng)成小樹(shù)林。同樣的光照、水分等狀態(tài)下,構(gòu)樹(shù)比其他一般的樹(shù)種生長(zhǎng)的速度會(huì)更快。構(gòu)樹(shù)的采伐周期約1年,本年栽種,可年內(nèi)收獲;一次栽種,可連續(xù)收獲。(據(jù)《中國(guó)大百科全書(shū)》綜合整理)
原以為構(gòu)樹(shù)最大的用途就是造紙,沒(méi)想到一身都是寶,成材快是為獨(dú)具的品格。
02
構(gòu)樹(shù)之“惡”
段后雷是我的朋友,土生土長(zhǎng)的成都人,他特別喜好植物。他的個(gè)人植物記憶里,對(duì)構(gòu)樹(shù)的泛濫有著銘心的總結(jié):每隔一天似乎都長(zhǎng)高一截,幾乎是看得見(jiàn)的瘋長(zhǎng),土地都不夠占了;結(jié)籽密集發(fā)苗很寬,一不留意,河邊橋頭、屋后林間、石縫墻根,到處都會(huì)長(zhǎng)出;環(huán)境適應(yīng)能力超強(qiáng),具有抗逆性,真算得上“野火燒不盡,春風(fēng)吹又生”。
讓段兄有些不服的是,就是這樣一種“雷鋒式”的英雄樹(shù)種,還是引來(lái)一些誤解與質(zhì)疑,古時(shí)竟冠以“惡木”名之。變著法子罵構(gòu)樹(shù),比較典型的,是寫(xiě)《水滸傳》的施耐庵。
《水滸傳》里武大本算不上什么角色,因武松、潘金蓮而路人皆知。武大的諢名叫“三寸丁谷樹(shù)皮”,照字面形容就是“矮只三寸”,面似構(gòu)樹(shù)皮色褐粗裂一般。此乃“三寸丁”和“谷樹(shù)皮”兩個(gè)綽號(hào)的連用,形容長(zhǎng)得矮小且丑陋難看的男子。
《水滸傳》第二十三回說(shuō)到:
這武大郎身不滿(mǎn)五尺,面目丑陋,頭腦可笑,上身長(zhǎng)下身則短;清河縣人見(jiàn)他生得短矮,起他一個(gè)諢名,叫做三寸丁谷樹(shù)皮。
卻說(shuō)武家兄弟在《水滸傳》中筆墨不少,施耐庵損人帶物,構(gòu)樹(shù)無(wú)端中這一招,也不知其冤也不冤。此處的“谷樹(shù)”即為“構(gòu)樹(shù)”。
清代著名詩(shī)人銅城派代表人物姚鼐,曾以《谷樹(shù)》為題,創(chuàng)作過(guò)一首七言律詩(shī):
《谷樹(shù)》
清·姚鼐
墻西生谷兩株連,陰蔽斜陽(yáng)媚夕煙。
惡木豈能妨志士,吾廬何厭?cǎi)毕s。
窗閑細(xì)響鳴秋籟,屋角新光照上弦。
幸假不才居隙地,清風(fēng)時(shí)為至江天。
不難看出,把“構(gòu)樹(shù)”稱(chēng)之為“惡木”的姚鼐,對(duì)構(gòu)樹(shù)也不太友好。
構(gòu)樹(shù)的名聲問(wèn)題,并不完全來(lái)自民間。很大程度上,它關(guān)聯(lián)著古代詩(shī)家對(duì)植物的文化審美。構(gòu)樹(shù)第一次被文字關(guān)注,循著時(shí)間長(zhǎng)河上溯,應(yīng)該是2500年前的事。
我們熟悉的《詩(shī)經(jīng)·小雅·鶴鳴》中,最早記錄有這樣一段:
“鶴鳴于九皋,聲聞?dòng)谔臁t~(yú)在于渚,或潛在淵。樂(lè)彼之園,爰有樹(shù)檀,其下維榖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”
其中的“榖”,就是古人對(duì)構(gòu)樹(shù)的叫法。“爰有樹(shù)檀,其下維榖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,意為所敘園中檀樹(shù)高枝葉密,下面的構(gòu)樹(shù)又矮又小。他方山上有佳石,可以用來(lái)雕美玉。
構(gòu)樹(shù)多為落葉喬木。初讀這一段,以為所寫(xiě)為灌木類(lèi)構(gòu)樹(shù)。后來(lái)又想,當(dāng)時(shí)人們看見(jiàn)構(gòu)樹(shù)速生,時(shí)常砍之,以免影響其它植物生長(zhǎng)。這意味著,先秦時(shí)期構(gòu)樹(shù)瘋長(zhǎng)的個(gè)性就已經(jīng)養(yǎng)成,這樣的“急性子”一直就沒(méi)有改變過(guò),且從那時(shí)起就開(kāi)始不受人待見(jiàn)了。
不然,為何“其下”呢?
春秋中葉的《詩(shī)經(jīng)》(約公元前6世紀(jì))在民間傳唱數(shù)百年后,到位西漢年間,毛亨、毛萇叔侄潛心為其作注,后人稱(chēng)為“毛詩(shī)”,毛氏所注的《詩(shī)經(jīng)》極具權(quán)威性,也就是直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流傳最廣的《詩(shī)經(jīng)》版本。
毛氏為構(gòu)樹(shù)的注釋?zhuān)瑯O為簡(jiǎn)明:“榖,惡木也”。鑒于《毛詩(shī)》的歷史文化地位,此論一出,一槌定音,構(gòu)樹(shù)惡木之名從此做實(shí),無(wú)有力辯。就算描述構(gòu)樹(shù)最多的《山海經(jīng)》,也限于其地理與物理視角,對(duì)構(gòu)樹(shù)文化符號(hào)的流傳,并無(wú)太大的影響。
毛氏將構(gòu)樹(shù)列為惡木,主要依據(jù)以上“檀”下“榖”類(lèi)之,取其上“善”下“惡”之意。當(dāng)然,古人嚴(yán)謹(jǐn),毛氏也借人之口,對(duì)江南用構(gòu)樹(shù)制造的宣紙,有很高的評(píng)價(jià)。只是他倆不可能知道,到了宋代,成都的楮紙還被朝廷指定為印制世間第一張紙幣的專(zhuān)用紙,那時(shí)印制“交子”的紙,就用構(gòu)樹(shù)皮制成,并因其不易偽造、磨損,給“交子”帶來(lái)“楮幣”之譽(yù)。
宋應(yīng)星在《天工開(kāi)物》中,介紹的造楮紙法十分詳細(xì),操作性強(qiáng),文中這樣寫(xiě)到:
凡楮樹(shù)取皮,于春末夏初剝?nèi) ち铮匀肽壑衤椋ㄖ窭w維,“麻”為形容詞)四十斤,同塘漂浸,同用石灰漿涂,入釜煮糜,然后漂洗、舂搗成紙漿。
樹(shù)已老者,就根伐去,以土蓋之,來(lái)年再長(zhǎng)新條,其皮更美。
交子的制作方法與宋應(yīng)星的說(shuō)法稍有不同,成都人沒(méi)有添加竹料,而是盡用楮皮。
南朝劉義慶在《幽明錄》中,開(kāi)頭便說(shuō):“漢明帝永平五年(62),剡縣劉晨、阮肇共入天臺(tái)山取榖皮。”有學(xué)者考證,“取榖皮”就是為了造紙。
榖,木名,即楮樹(shù),也就是成都人眼里的構(gòu)樹(shù)。《說(shuō)文》亦云:“榖者,楮也。”根據(jù)劉郎傳奇推斷,公元一世紀(jì)就以楮造紙。當(dāng)然,這種說(shuō)法目前還有爭(zhēng)議。不過(guò),在《幽明錄》作者所處的南朝,試著用楮造紙應(yīng)該是有可能的。也因?yàn)榇耍陀辛撕髞?lái)蘇東坡的名句:“嬌后眼,舞時(shí)腰,劉郎幾度欲魂消”。
“惡木”也不全是構(gòu)樹(shù)的獨(dú)有標(biāo)簽,比如皂角樹(shù)。公元761年,杜甫寓居成都草堂,作有《惡木》一詩(shī),發(fā)出“常持小斧柯”,“惡木剪還多”的感嘆。這里的惡木當(dāng)然不是指構(gòu)樹(shù),而是雞棲樹(shù),成都人稱(chēng)之為皂角。杜甫在這里借物言志,不滿(mǎn)當(dāng)朝壓制賢良。
唐宋以來(lái)的文字,唯蘇軾意欲重墨為構(gòu)樹(shù)立言。他曾留下過(guò)《宥老楮》一詩(shī),此詩(shī)雖長(zhǎng),但幾乎句句與構(gòu)樹(shù)關(guān)聯(lián):
《宥老楮》
宋·蘇軾
我墻東北隅,張王維老谷。
樹(shù)先樗櫟大,葉等桑拓沃。
流膏馬乳漲,墮子楊梅熟。
胡為尋仗地,養(yǎng)此不材木。
蹶之得與薪,歸以種松菊。
靜言求其用,略數(shù)得五六。
膚為蔡侯紙,子入桐君錄。
黃繒練成素,黝面颒作玉。
灌灑烝生菌,腐余光吐?tīng)T。
雖無(wú)傲霜節(jié),幸免狂酲毒。
孤根信微陋,生理有綺伏。
投斧為賦詩(shī),德怨聊相贖。
東坡先生博學(xué),想必對(duì)《本草經(jīng)》之類(lèi)著作描述構(gòu)樹(shù)的功用爛熟于心。本想挖去這棵不材的老構(gòu)樹(shù),怎奈聯(lián)想其皮可制紙?jiān)觳迹苋胨帲€可輔助自己的烹飪手藝,也就罷了。最后投斧賦詩(shī)去,徒生出對(duì)構(gòu)樹(shù)德怨兩抵、暫且宥之的心緒。
蘇軾以怨入筆,本想為構(gòu)樹(shù)說(shuō)幾句好話(huà)。卻一改平常恣肆豪放本色,反以白描般手法寫(xiě)實(shí),也讓人感到其字里行間的猶豫與糾結(jié)。如果權(quán)且算作一辯,此辯全無(wú)“榖,惡木也”的干脆利落,也未能給構(gòu)樹(shù)之名帶來(lái)大的反轉(zhuǎn)。
好在構(gòu)樹(shù)全然不顧這些人間的是是非非與糾葛纏繞,也不看任何人臉色行事,不管褒也好,貶也罷,均泰然處之,一味地由著自己性子任性瘋長(zhǎng)。它是要用自己的行動(dòng),長(zhǎng)出一個(gè)由自己創(chuàng)造的新世界來(lái)。所以,到了蘇東坡的時(shí)代,這時(shí)的構(gòu)樹(shù)終于成為了人們眼中的主角,搖身一變成了交子的原料,無(wú)論是物理空間還是意識(shí)空間,在成千上萬(wàn)年的不懈爭(zhēng)取和努力之下,其待遇當(dāng)然應(yīng)該好多了。
自然地、野性地、不問(wèn)原由地生長(zhǎng),也許就是構(gòu)樹(shù)的天性。愛(ài)物及烏,或許,也成為后來(lái)不少文人喜歡楮紙的原由吧。
來(lái)源:成都方志
(本文節(jié)選自《1024-2024,世界第一張紙幣交子誕生地成都,以及千年來(lái)的世界》(三卷本)之上卷《一張神奇的紙幣》“第01章從一株樹(shù)的側(cè)影,尋覓紙的方位”。)
(作者:章夫中國(guó)作家協(xié)會(huì)會(huì)員,成都市作家協(xié)會(huì)副主席,享受?chē)?guó)務(wù)院特殊津貼專(zhuān)家,四川省第13批學(xué)術(shù)與技術(shù)帶頭人,“天府青城計(jì)劃”(天府文化領(lǐng)軍人才)入選者,第十批成都市有突出貢獻(xiàn)的優(yōu)秀專(zhuān)家,首屆四川省十佳新聞工作者。)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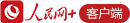



 第一時(shí)間為您推送權(quán)威資訊
第一時(shí)間為您推送權(quán)威資訊
 報(bào)道全球 傳播中國(guó)
報(bào)道全球 傳播中國(guó)
 關(guān)注人民網(wǎng),傳播正能量
關(guān)注人民網(wǎng),傳播正能量